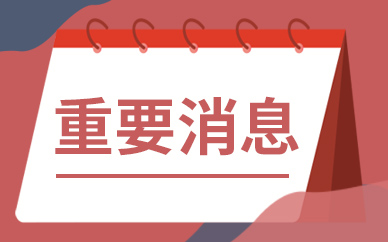苏钢和同志们
苏钢1920年出生于山东,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1月在延安入党,曾任贵州省委书记、省长、省顾委主任。陆学清于曾在苏钢身边担任秘书工作17年,耳濡目染,所见所闻,深为苏钢的党性风范所感动。下面是陆学清所亲历的一些事情。
1977年3月,苏钢从鱼米之乡的湖南调到贵州工作。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正值“文革”后期,贵州百废待兴,工作十分困难。他深入基层,依靠群众,排除万难,重点抓了水城钢铁厂的扩建、乌江渡水电站和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的建设,后来又重点抓贵州农业。
1991年6月下旬,贵州全省暴发特大洪灾,铜仁地区尤为严重,苏钢执意要去铜仁了解灾情,为群众排忧解难。
当时从黔南方向去铜仁的道路被洪水冲断,便决定绕道遵义去。7月5日,车行至遵义县三合川黔线121公里处,公路被洪水淹没,水茫茫一片无法通过。
当时遵义地区的领导赶来迎接苏钢一行,也因水阻过不来。有的同志建议返回贵阳,另谋它路,苏钢坚定地说:“不行,那样就要耽误几天时间,救灾如救难,怎么能返回去呢?即使游泳也要游过去。”
围观的干部群众见此很受感动,找来当地农民用的打谷斗给苏钢漂渡。但在汹涌的洪水中用谷斗漂渡,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随行人员都在犹豫,苏钢却斩钉截铁地说:“行,就这么办,越快越好。”
陆学清说:“打谷斗小,水大,漂渡十分危险,万一翻了……”
苏钢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万一翻了,我会游泳。”说罢带头爬进打谷斗。打谷斗在汹涌的洪水中颠簸,险象丛生,但苏钢镇定自若,经过奋力拼搏,终于到达彼岸。苏钢时年七十有二。
来接苏钢同志的遵义地区领导无不为苏钢同志以工作为重,以人民群众疾苦为重,不计个人安危的精神所感动。
视察完遵义的灾情后,苏钢马不停蹄赶到思南,立即深入农户,详细了解受灾户的情况,并找来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他们商量送衣送粮,尽快解决受灾农民的燃眉之急。
他对干部群众很关心。
“文革”结束之初,不少干部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有一些老同志,被打成右派,也没有恢复工作,还被开除党籍。苏钢听说了以后,总会亲自去走访,作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最后很多同志都获得了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
有一位“文革”前的正厅级干部,解放前做党的地下工作,人称是贵州的华予良,当时还没有被平反。有一天夜里苏钢带着秘书去看他。他住在小十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房子很破旧,苏钢深夜走访,老同志十分感动。
曾有一位处长告诉曾在苏钢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他最近见到苏钢同志,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的名字,关心地询问他现在的工作,家里的情况,他很受感动。
苏钢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没有党的教导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没有人民的哺育我就不能健康成长。我的一切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
“文革”期间,苏钢受到迫害,停发工资,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粉碎“四人帮”后,补发了全部工资,这笔钱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苏钢分文不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他住的院子,办公厅多次提出修整,苏钢坚持不肯,说节省一分算一分。他家的沙发都是50年代的,修了又修,补了又补,办公厅要给他换新的,也被一口谢绝,他说:“只要整洁就行,破了修补一下即可。”
1996年洪水淹到他家二楼,沙发、家具被水一泡全散了,无法再修补,他不要国家配给,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己掏钱买了些最普通的沙发和家具来用。
中央规定省级干部可买230平方米的住房,省里决定给省级干部修建住房。苏钢马上给省委写信表示不买房子,说国家并不富裕,住房困难的人还不少,我们老了,孩子们有自己的住房。孩子们要让他们自己去奋斗,没必要留一套给他们。普普通通的几句话显示出高风亮节。
其实只要他点点头,动用存量补贴,不花多少钱即可得一套价值上百万元的私房,不仅可以自己享受,还可以传之后代,可他谢绝了。
他仅不向党和人民伸手,而且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捐献出来为党为人民办事他将自己毕生节约下来的148200元和向子女借的1800元,凑足15万元捐献给了家乡的学校建图书室,为培养下一代出力。
他说:“家乡父老养育了我,可我没为家乡父老说一句话,办一件事,心中有愧。这点钱不能解决大问题,只是聊表寸心。”“借孩子的钱,从今后的工资中节约出来慢慢还清。”
平时,苏钢只要知道哪里有灾情,他都成百上千的捐款。见到报刊上有需要救助的,就解囊相助。捐款由陆学清送到报社或直接送到受助人手中,而且不许留名,不让采访,只说是一对老夫妇的资助。
去的次数多了,报社的同志才知道是苏钢夫妇。他最早带头资助了8名失学儿童从小学读到高中。并说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资助他们完成学业。
他的日常生活十分简朴。他不喜饮酒,不喜奢侈浪费。每天早餐,就是一碗稀饭,一盘咸菜,再就是一个热馒头,或者吃面条;中午吃米饭,晚上吃面食。如果下去到县里,到工厂视察,人家摆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就非常反感,往往扭头就走,要求撤摔酒席,态度非常严肃。在视察的路上就餐也很简单,往往就在街边的小店,只要干净、卫生就行,毫不讲究。
他的一件衬衣从湖南穿到贵州,20多年了还舍不得丢掉。有时还穿补巴裤子。有一次在网球场上,大家见他穿着补巴裤子,开玩笑说:“你还穿补巴裤子,我们早就不穿了。”可他并不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很坦然。
苏钢在湖南接到调贵州工作的调令,二话没说,便走马上任,不带任何随员,连夫人都没有带,只带了一个小孩到贵州。
他的子女都有大专以上学历,但没有一个安排在党政机关,都在工厂和基层单位。他带来的小孩就安排在贵钢子弟学校教书。还有一个从湖南大学毕业后苏钢支持她去西藏,后因身体关系从西藏回到贵阳,被安排在中曹水厂当一名施工员。安排子女进党政机关工作,对于他来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一次,省委在市郊一个农场开会,恰逢农场水蜜桃丰收,农场给每位领导送了一筐桃子,秘书考虑到每个领导都有便自作主张收下了。
回到家后,苏钢发现了这筐桃子,质问桃子是怎么一回事。秘书如实相告,苏钢听完后很不高兴,严厉批评了秘书,并责令将桃子送回去。这事以后,苏钢严肃地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以后不经同意任何人不许收任何礼物。
一家工厂的领导来看望老领导,送了两瓶茅台酒,客人走后苏钢即令陆学清送交省纪委,
这种作风直到离休后依然如此。每年春节来看望苏钢的人不少,按中国人的风俗,送点年礼,人之常情,苏钢却坚持不受。后来干脆每年春节前在大门上用红纸写上“欢迎探视,谢绝年礼,敬请合作”。而且嘱咐门卫,凡见带礼的来客,一律把礼物放在门卫处,待他们出门时带回去。即使苏钢因病住医院,老部下送点水果、奶粉之类的食品,苏钢也婉言谢绝,一概不收。
苏钢从不用公车办私事。老伴因病去医院,坚持要陆学清按公里数把钱如数交到车队。接送亲友更是如此,每次交费少则几十元多则上千元。
苏钢对工作十分严肃负责,对部下和家人要求严格,可待人接物十分和气。陆学清在他身边工作17年,从未见他对任何人发过火,骂过人。对别人的错误虽然严肃批评,但都是轻言细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他凡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亏待别人。
每次出差在外吃饭也总是苏钢掏钱,他说:“我的工资高,我付账。”凡是和他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都为他人的格魅力所感染。